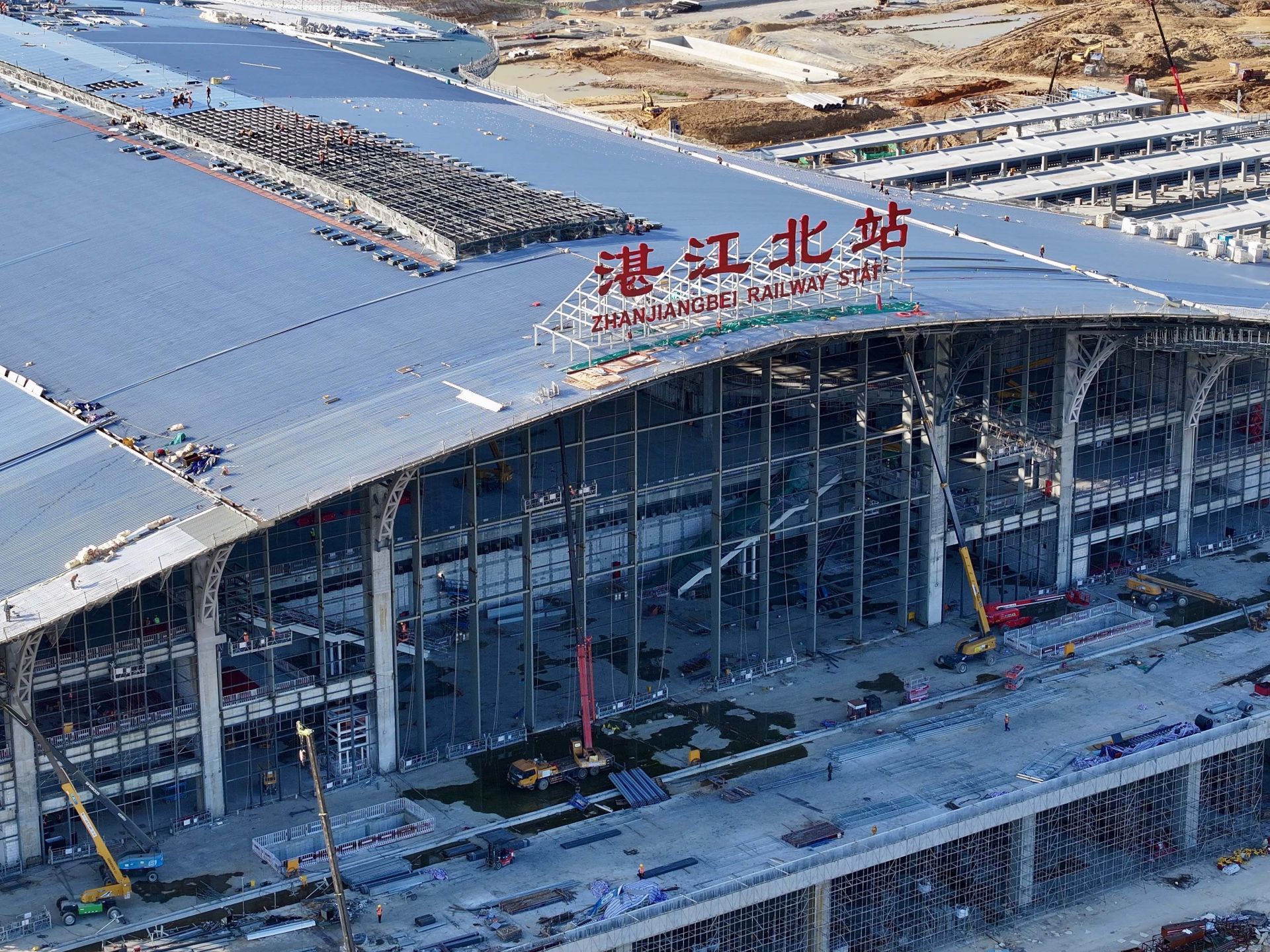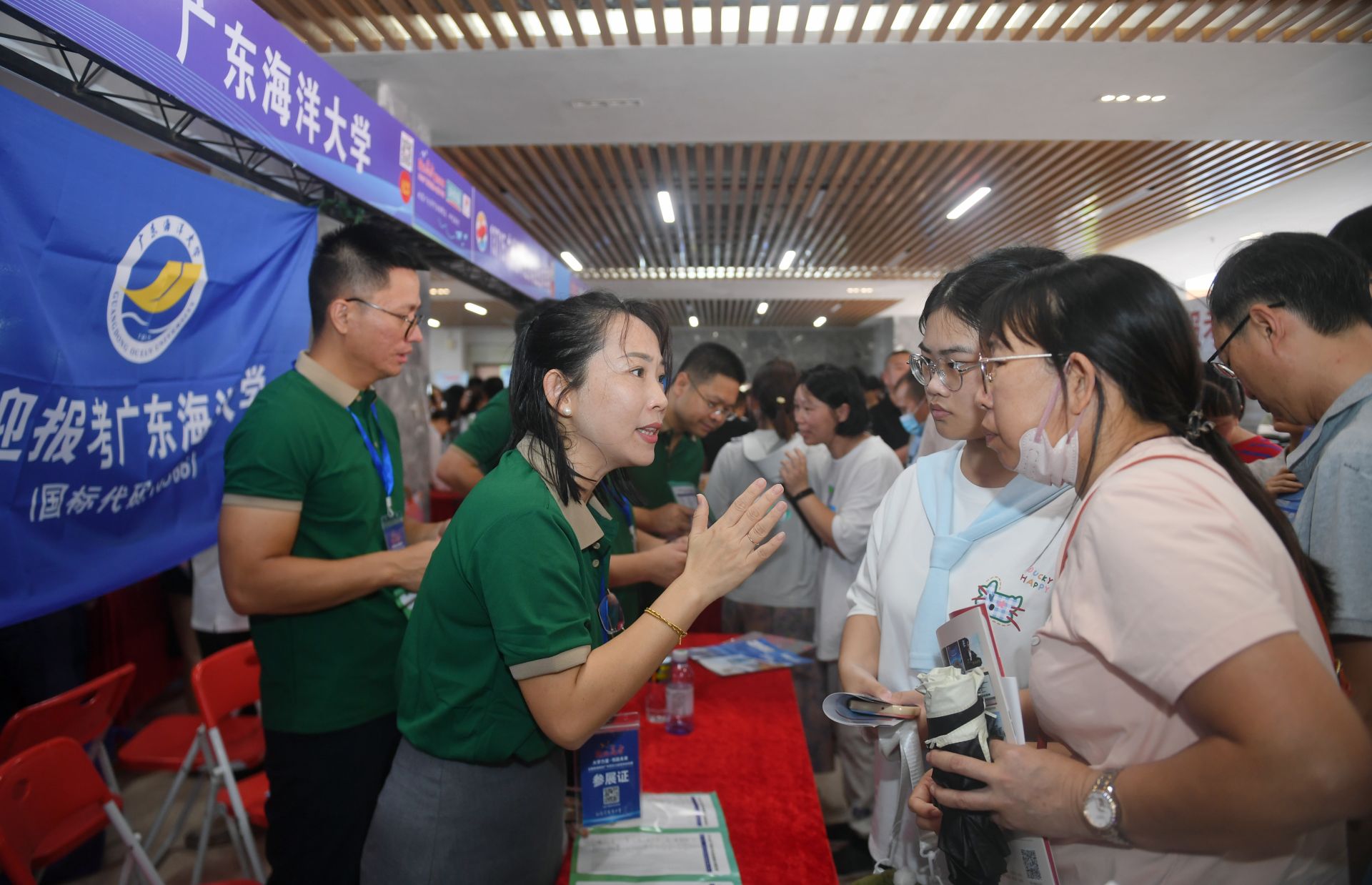福田河極窄,一灣清水托著兩岸的樹木。蒲桃居多,開白色的帶著絨毛的花,以手撫之,柔柔的;偶有幾顆洋蒲桃,開粉紅的帶著絨毛的花,以手撫之,柔柔的。春天的時候,二者以花色區(qū)分。夏初,它們以果實區(qū)分。蒲桃的果實像一個乒乓球,黃綠色,裹著硬硬的核。據(jù)說可以吃,但我從沒嘗過。吾有一簡單判斷,所謂水果,市場上應該有售。若否,定有巨大缺陷,輕易別碰。洋蒲桃的果實洋紅色,呈梨形或圓錐形,頂部凹陷。夏日南方市場常見,人稱“蓮霧”,口感清甜,味淡,像霧像云又像風,名稱中帶一“霧”字,堪為點睛之筆。
還有芒果樹。該物過于普通,若無果實點綴,不論給它冠以何名,它都無法理直氣壯地反駁。如今,懷揣一堆長到半大的芒果,它似乎有點底氣了。那些芒果圓鼓鼓的,簡直不像芒果(起碼形狀上要細長些嘛)。被一根根細繩吊著,青色,青澀。它很決絕,一意向旁邊的蒲桃看齊。
荔枝樹的枝干黑而粗糲,七扭八歪,與其他樹木比起來,它對人類的善意最明顯,因為這種姿勢有利于人類攀上高處采摘果實。可是果實呢?抬頭望,樹上的荔枝真小,三五成群,堪比手指肚,綠色,無積極進取之勢,陽光揉搓它們身上那一個個小疙瘩,似在鼓勵。那邊廂卻無動于衷,一副懨懨的樣子。幾天過去,再見時,綠荔枝有的干枯而死,有的掉落地面。
菠蘿蜜掛在樹干上,本該又長又圓的它們,長成了歪把子狀,形容怪異,像是被誰打了一拳,凹進去一塊,然后凝固了。其中一個還蒙著一層薄薄的白棉絮。旁邊的木棉樹筆直地扎向天空,一副不干己事的姿態(tài)。它已經(jīng)把種子甩掉,種子隨著棉絮飛向哪里,落在哪里,全是春風的安排。
一個人躺在一棵樹的樹杈中間,兩只手架著手機,保持這一個姿勢久久不變。暖風從水邊漾上來,經(jīng)過樹林過濾,變成了涼爽的風。幾個幼兒園的小朋友,每人騎著一輛小車,在老師的帶領(lǐng)下,排著隊魚貫而過。清清爽爽的臉蛋,干干凈凈的衣服,在顯示他們都是意料之中的果實。
而樹上的那些,被定義為不成器的果實。它們知道自己是綠化樹,只管在河岸上敲邊鼓,不承擔為人類提供食物之責。有一些果實是可以吃的,但轉(zhuǎn)頭看看其他果實,放蕩不羈,汪洋恣肆,也便不再繃著了,跳離了世世代代的規(guī)則,向著那一群自由的同伴跑去。
地上盡是果實,在路邊,在草叢里,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,要么渾身上下都是裂開的縫,要么爛掉了半邊,要么被誰踩了一腳,果核滾落,稀稀的黃色湯汁四處流淌。芒果黑灰,上面布滿一個個斑點;蓮霧扎在一根細小的枯枝上,粉嫩的外皮傷痕累累,我試著將其拔出來,卻露出一個觸目驚心的窟窿,趕緊又插上。木瓜癟癟的,有皮無肉……清潔工每隔一會兒就要往復一次,把剛剛掉下的果實掃到一起,倒進垃圾箱里。即便如此,他們也收拾不干凈。果實什么時候掉下來,沒個規(guī)律。久而久之,清潔工也懈怠了。
豐收季節(jié)已到,就讓它們跟著天時運行吧。
深圳二十四橋
石巖湖本一大湖,山間一片浩瀚的水,周圍森林環(huán)繞,密不透風。其為水源地,游人無法實際接近。站在高處,遙見藍色翡翠。風吹樹搖,翡翠碎裂滾動,漸漸蔓延上岸,不洶涌,卻扎實,越過植物,遇坑洼與溝壑,留下深深淺淺的一汪,再挪不走。一個夜晚過后,各類痕跡抹去,草仍綠,樹亦高聳。大湖還是大湖,周圍多了一個個小湖,闊者幾百平方米,窄小不過其三分之一。
此為石巖湖濕地。
不似大湖包羅萬象,小湖各有分寸,強調(diào)專業(yè)性。一湖中矗一小島,島上長滿蒲棒,如超大綠釬子上穿著超大烤腸,根根射向天空,觀感結(jié)實,摘下一根來可以當武器揍人。一湖中飄滿睡蓮,花未開,葉片擁擠疊加,無聲勝有聲。另一湖,略小,水面亦睡蓮,而葉片變小。它們好像精心計算過,多大的湖面配多大的葉片。造物非神奇,是“懂得”。一湖干凈無物,倒影著周圍的樹木,波心繁茂森然,以虛空至全有……
湖與湖間,一條條長廊。廊木上綁著枝條,綠葉與各色花朵抖抖索索。人行其間,觸手可及,更可湊近聞香。其中一條長廊,滿是禾雀花,乃吾最愛之一。此時是初春,禾雀花尚未開放,眼中仍見一只只豆青色的鮮活小鳥排列其上。我見花,花總在。這些植物絕對沒有建筑命長,一年一開,一季一謝。再過些年,若長廊還在,主事者的興趣可能是炮仗花、簕杜鵑或其他什么什么,一夜之間便可更換。而游人茫然無知,在他者的個人偏好中游蕩,同化為自己的小歡喜。
大湖神秘、淡定,甚至顯得遙遠,非航拍不見真容。小湖非單一拱衛(wèi)者,再外圍,為一巨大地盤,地盤上有小河一條。是一條還是幾條,一直沒搞清,彼此交叉,首尾相連,蛇頭吞蛇尾。再遠處便是鐵硬的馬路,滾滾都市在另一邊晝夜運行,商業(yè)、生產(chǎn)、鉆研,完全是不同的世界。
小河寬不過三五米,不足以呈現(xiàn)時光,岸邊一簇一簇的狼尾草和白頭蘆葦被陽光照耀著,為其抹上一點滄桑。水中偶現(xiàn)成片綠藻,具死水特征。風來,一會兒向左,一會兒向右,并非坡度令其動起來,而是風。水一動,又像是活水。河水的內(nèi)核是流動嗎?不,是橋。偌大空間上,道路恣肆,在一片綠草地上閉著眼走,橫七豎八,遇到了水,輕輕一躍,身后拉出小橋一個。路的任性,成就了一座座橋。
紅色的木質(zhì)橋,白色的小石橋,均不長,長則二三十米,短則幾米。多數(shù)平鋪,亦有拱橋。二十四座橋均有名:藍楹橋、纓丹橋、金葵橋、荔香橋、鳳凰橋、半蓮橋、落杉橋、風鈴橋、琴葉橋、石榕橋、壓堤橋、鎖瀾橋、跨虹橋、映波橋、望山橋、掬溪橋、涵芳橋、蟬鳴橋、青螺橋、白鷺橋、百雀橋、彩蝶橋、梭魚橋(汀步橋)、匯溢橋。
看對稱度、組合度、排列式,這些名字一定是經(jīng)過了仔細推敲。但放在更大的空間上,又定是隨意的。為何稱百雀不稱千雀,叫跨虹不叫拭虹?弱水三千,只能取其一瓢,略去兩千九百九十九瓢,不止。推敲仍是隨機。而這隨機的命名,對橋產(chǎn)生了影響。它會按照名字的指引,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恰如一個小名叫秤砣的孩子,長大一定結(jié)實。
白鷺橋旁,立著幾棵落盡葉片的瘦樹,枝條根根獨立,一只白鷺站在分枝上。夕陽將沉,用手機逆光拍照,鏡頭中只有黑白二色,如同動畫剪影。盯好久,白鷺也不飛走。偶爾在枝頭展翅,河水便蕩一蕩。起名前,白鷺尚在遠方;起名后,白鷺聽從了神諭,一個接一個到來。橋名與周邊事物不一定實打?qū)嵶肿窒嗫邸?梢怨テ湟稽c,可以無限外延,可以取其意涵,搭邊兒即可。藍楹橋邊一定要種一棵藍楹樹嗎?多蠢!一個叫藍楹的女孩子在那里坐一會兒,橋便有了名字。荔香橋無需穿越茂密的荔枝林,此前本地有過荔枝林,后來被砍掉,香味仍在。青螺橋下也不一定要擺幾個螺殼,有人在這里吹過小螺,人走了,余音數(shù)年不散。那么多的橋,最初的命名,如嬰兒命名,冥冥之中被天意點了一下。新興城市如深圳,一切都在變化中,今是昨非,大拆大建。不要因人而變,再改來改去。這些名字握在一起,堅定地相信世界會更好,游人會給它們祝福,而它們,必將越來越與自己的名字吻合。
清晨的露水在草尖兒上猶豫不定時,有人走過來,踏上橋,露水掉落,仿佛發(fā)令槍,橋和橋就開始說話了,彼此傳遞看到的人和信息。
若干高出地面的小丘陵,分布于濕地橋間。中年男子帶著一個孩子,站在頂端放風箏。掛在樹枝上的一個碎裂了一半的風箏,與天空飄搖的風箏遙遙相望,彼此不說“我就是你”。小女孩兒在丘陵林中奔跑,小裙子一閃一閃,尖叫聲不斷。一些騎行者帶著統(tǒng)一的白帽子,飛快地在紅色車道上掠過,別盯著車輪看,旋轉(zhuǎn)得令人暈眩。老年人光著膀子迎面跑來,衣服搭在胳膊上,汗毛被樹葉中間滲透下的晨光照得晶瑩發(fā)亮。一個小男孩騎著自行車,另一個更小的男孩在后座上抱著他的腰,問,哥哥,你吃過XX嗎?風把“吃過”后面的字吹得七零八落,無法聽清。安在地面上的噴水槍不斷轉(zhuǎn)圈,不小心從下面經(jīng)過,接了一身的水。噴水槍若無其事地轉(zhuǎn)向另一面,這邊的人一邊整理濕淋淋的頭發(fā),一邊互相看著對方哈哈笑。
一大一小兩個人,坐在望山橋上,大人的腿搭在“山”和“橋”之間,仿佛一個標點符號。小孩兒對著大人不停地說話。那座橋馱著一個家庭,那個家庭給橋注入了血液,令其鮮活。每一個走來的人,每一個三三兩兩的人群,都會留下一個個身影。他們離開了,身影永久地印在這里,一個一個疊加,就成了一個氣場。
江南已有著名的二十四橋,深圳這二十四橋不怕人說山寨嗎?在山寨基礎(chǔ)上超越,或需付出比原創(chuàng)更多的心血。接納、借鑒、提升,文化的一體兩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