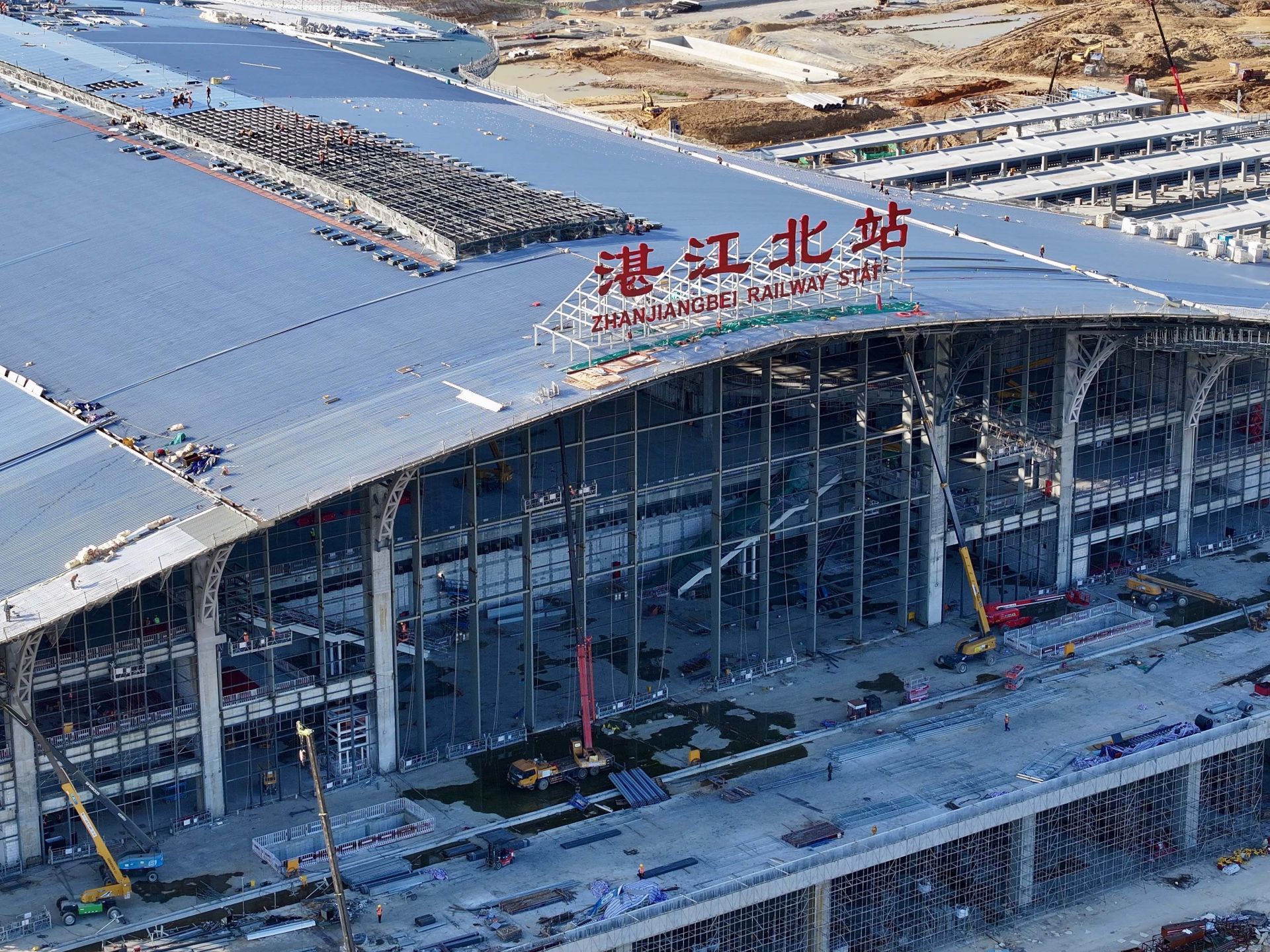陳寶國分享演藝經驗。視覺中國
白玉蘭電視劇評委會主席大師班昨天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。本屆電視劇類別評委會主席、演員陳寶國與兩位評委——編劇高璇和導演、編劇康洪雷回首藝術之路、暢聊行業新變。
陳寶國是繼2016年張國立之后又一位主職是演員的白玉蘭評委會主席。他曾拍攝《大宅門》《茶館》《老酒館》《北平無戰事》等70余部電視劇作品,多次入圍和獲得白玉蘭獎。
年輕一代起來了
本屆電視節,陳寶國很忙。當天上午他剛參加了兩場論壇,下午又來到評委會主席大師班現場分享干貨。陳寶國說,自己已經看了20多天片子,每天不由自主看到凌晨三四點。“今年入圍的作品整體呈現高水準,今年不是小年,是大年,不好評。”
他認為,如果電視劇可以分代,這批入圍作品的創作者,應該是中國電視劇界的新一代,青出于藍而勝于藍。康洪雷也有同樣的感受。“觀片的兩個多月里,我看到了青年工作者的工作能力、審美方向和對家國情懷的關注,作品不僅是強情節、強沖突,還有在人文情懷、家國情懷上的審美自覺,非常可喜。”
今年上海電視節迎來第30屆,康洪雷曾多次參與白玉蘭獎角逐,也做過幾次評委,他發現電視節變得越來越國際化,入圍作品的藝術水準逐年攀升。
“這是一個充滿自豪感和可信度的平臺。”高璇的作品兩次提名白玉蘭獎,一次獲獎,今年第一次當評委,“白玉蘭給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刻,它在行業里已是最專業、最權威,從業者最想爭取的獎項之一”。
談到當下長短劇之爭,康洪雷說:“重點是作品的關注度和靈魂深處的共情。我不在乎長,只在乎內容。”高璇也認為,劇沒有長短之分,只有好壞之分,“故事有自然的長度。短劇和長劇不是對手,可以并存。短劇普遍需要精品化,但邏輯、人物完整度上有欠缺。長劇永遠不可替代的是表達的深刻和人物的復雜,也因此,長劇永遠不可能消亡”。“同意!”陳寶國說。
生命力來自劇作
在大師班上,不少觀眾抓住與名家面對面的機會,向陳寶國表達了對他作品的喜愛。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后,陳寶國立志當一個好的性格演員,突破自身限制,挑戰不同的角色類型,賦予人物獨特的藝術生命力。曾經,《四世同堂》《神鞭》兩部作品同時找他演,前者是演封建大家庭里的大少爺,后者是演底層的碼頭混混,“必須二選一,我選了后者,前一個類型的角色總覺得以后還能碰到,但后面的角色可能這輩子就一次機會”。
從藝40余年,陳寶國塑造了很多觀眾心目中的經典角色,社交平臺上,不少年輕觀眾用新的方式去傳播和解讀,甚至有人在漫展上COS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的嘉靖帝。“《大明王朝1566》是一個群像戲,所有演員都在飆戲。我們住的招待所,晚上亮著燈,鴉雀無聲,大家都在樓道里做功課。到了拍戲現場,基本沒有人帶劇本。”陳寶國說。
談到經典影視劇在當下被反復重溫,他將其歸功于劇作的成功。“演員要靠角色說話,角色從劇本里來,劇作最重要。電視劇要保持旺盛蓬勃的生命力,繼續往前走,就是靠劇作。我看到《大宅門》劇本時就感到,這個劇本‘五十年一遇’,能遇到這個角色是我的幸運。”與知名編劇高滿堂合作六次,同樣是他眼中的一大幸事,“我在他的戲里演過工人、士兵、農民、商人、中醫等,體驗不同的戲劇人生。能與這個時代的大師們合作,飾演他們作品中的角色,作為演員,我很幸運,也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。”
在現場,他向幾位嘉賓現場“求戲”。“演員到了一個年齡段,就只能演這個年齡段的作品,我這個年齡段的戲不多,請多寫點。”得知他要做性格演員,曾有知名評論家對他說,“你志向很大,挺不容易,但你這條路很難,也很長,也許不到十年就會后悔”。如今40多年過去,陳寶國仍覺得這條路前景光明,“我想永遠在路上”。(解放日報 記者 鐘菡)